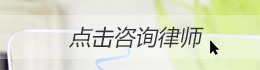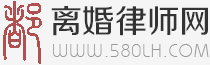現行《繼承法》第10條第一項規定,我國法定繼承第一順序繼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該法第12條規定,對公婆或岳父岳母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喪偶兒媳或喪偶女婿,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在法定繼承中,將配偶以固定順序規定為第一順序,存在的問題是:
從理論上觀察,這樣規定第一繼承順序不具合理性與正當性。各繼承人與被繼承人的關系各異。配偶是關系最為密切的親屬,它是血親的源泉、姻親的基礎,產生于婚姻關系。子女、父母與被繼承人之間是一親等的血緣關系,而對公婆或岳父岳母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喪偶兒媳或喪偶女婿與被繼承人之間卻是姻親關系。雖說現代繼承法已經突破僅將血緣關系與婚姻關系作為繼承權產生基礎的立法傳統,將特定的扶養關系也作為繼承權產生的基礎,但同時將三類與被繼承人關系完全不同的人納入同一繼承順序,這樣規定既不屬于親等繼承制,也不屬于親系繼承制,其合理性與正當性值得懷疑。
從實踐中觀察,這樣規定第一繼承順序會造成剝奪其他繼承人繼承權的后果。在法定繼承中,配偶一方死亡,其沒有子女也沒有父母的,第一順序繼承人就只有配偶一人,不論第二順序繼承人有多少,都不會發生第二順序的繼承問題,因此,死者的遺產就被配偶一人全部繼承,這等于在事實上剝奪了第二順序繼承人的繼承權。這樣的規定合理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的汪楣芝繼承案,就能夠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該案中,楊某是1949年去臺灣的老兵,一直未婚,其20世紀80年代末回鄉探望在北京的哥哥及其他親屬,經介紹與汪楣芝相識結婚。婚后,楊某用在臺灣幾十年積攢的錢,買了商品房和家庭生活用品,尚余30多萬元現金。不到一年,楊某病故,楊兄與汪楣芝討論繼承問題,主張將房子、生活物品及部分現金由汪楣芝繼承,楊兄與其他親屬繼承部分現金,汪楣芝不同意這個分配方案。楊兄訴訟到法院,一審法院按照這個方案作了判決。汪楣芝上訴,二審法院仍然判決楊兄及其他親屬繼承部分現金。毫無疑問,這樣判決是違反《繼承法》關于繼承順序的規定的。后來該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案件判決后社會反響很好,沒有必要重審改判,最后該案不了了之。這個案例說明,配偶法定繼承為第一順序,有時會出現其他親屬不能繼承遺產的后果。試想,楊某與楊兄是親兄弟,而其與汪楣芝的配偶生活不到一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將楊某的遺產全部由配偶繼承,顯然于法有據而于理不通。該案判決沒有按照配偶第一順序的規定,實際上是將配偶作為零順序對待,但如此判決更加合理,收到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應當看到,我國目前實行的繼承制度存在較大的局限性。這是由于立法當時受計劃經濟條件的限制,公民個人的財產數量不多,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建立,遺產主要用于保障實現家庭的養老育幼功能。同時,立法當時關于繼承法的理論基礎準備不足,缺乏必要的論證。立法將配偶、子女、父母以及對公婆或岳父、岳母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喪偶兒媳或喪偶女婿這四類不同關系、不同類型的人放在同一繼承順序即第一順序,在私人財產尚不豐富的社會發展時期尚能解決我國的遺產繼承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的迅速發展,在個人對財富追求的積極性極大提高、個人財產顯著增多的情況下,決定我國遺產具體分配流向的法定繼承順序規則日益凸顯其不合理之處。公民個人對財產權利的重視及對自由權利的追求要求財產分配、轉移、繼承的規則能隨著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得到調整,以便更充分地體現被繼承人分配遺產的意愿,公平、合理地分配遺產。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隨著經濟、社會、家庭結構與模式的發展變化,對法定繼承人的范圍及順序都進行了相應調整,有的擴大了法定繼承人的范圍,有的對法定繼承人的應繼份進行了調整,有的將配偶間互為繼承人的順序以彈性的方式進行了規定,以平衡配偶與其他法定繼承人之間在法定繼承時的利益關系,緩解法定繼承中存在的矛盾。在我國《繼承法》的修訂過程中,也應當對配偶法定繼承的第一順序進行改革,避免出現前述問題。